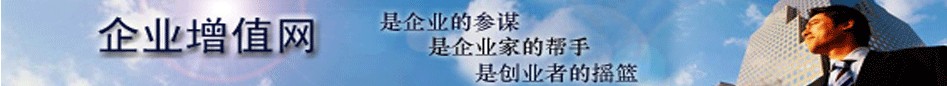人口红利的变化可以引起一系列的变化,首先是改变储蓄、投资为主的资金结构,因为全社会可能面临赚钱的人少、被赡养的人多的局面;其次,支撑国民经济的建筑业会变化,住房问题是一级推一级的,最底层往上推,到中产阶级到富裕阶层,假设城市人口未来几年增长速度慢了,算算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什么水平了?因此,建筑业高峰已经过了,不可能再上涨那么快。另外,农民的问题解决难度更大,因为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给他们。
第二大变化就是出口结构性调整比较大,虽然今年恢复比较猛,但是要维持30%以上出口增长率,我认为太难。因为中国生产,欧美消费的模式不能持续,这对于中国和外国都是一种失衡状态。
第三大变化是我们的经济领域还没有完成一些重大改革。比如要素价格改革,首先是土地,改革初我们认为资本是稀缺的,土地不是稀缺的,所以用廉价的土地换取资本,未来土地真正的价值反映出来的话,企业价值就会发生变化,国民经济也会发生变化,靠土地来维持的地方财政也要发生变化。另外资本价格此前也是长期维持在低水平竞争,这样不能持久的。此外,能源长期保持高价格,矿产资源税没有到位,通讯资源、航空运输的空中资源也未完全反映市场价值。另外还有劳动力成本,尽管有《劳动合同法》了,但有没有落实?是不是能够保证农民工的利益或者是工人的利益?劳动力正在争取但还没有完全反映其价格。还有公共事业的产品价格,水、电、气也没有到位。此外,经济发展中的安全成本,环保成本等都要考虑。
我认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,特别是前十年释放了很多生产力,用的是增长红利和劳动生产力的红利,企业可以不断地进行新投资,不断地回收。如果增长因素放缓了,这些都要发生变化。从人口红利到外部的变化,及社会要素价格的改变,是前三十年没有触及的,现在有的是发生了,有的会慢慢发生,我认为在未来十年都要发生。
《21世纪》:要素价格改革已经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了,更多需要政治领域的改革才能推动吧。
秦晓:我觉得要素价格还不是政治领域的问题,跟政治领域更相关的是政府职能的改变。
但是在政治领域,可能有一些利益集团不愿意动,既然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市场经济的目标和方向,市场机制的核心就是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定。现在有人质疑要素价格市场化,只不过是说什么时候市场化,以多大的速度进入市场化。
下个三十年:公共领域三大挑战
《21世纪》:那么在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领域,新的三十年面临哪些问题、需要哪些变化?
秦晓:第一个,我们面临着制度化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的挑战。这是改革必经的阶段,当年美国针对这个有过“进步运动”,其他国家也曾有。这个问题有经济不发达、文明程度不高的原因,但如果贪污、潜规则制度化了,其根本原因是行政权力和资本相结合。
权力和资本应该是分开的,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,手里不能有这么多经济资源,我不是指财政,而是指经营品。这关系到政府职能要不要改?我觉得未来三年。人们的容忍度是有限的,不愿意看到贪腐变成“制度”。
第二是农民的问题。在未来,农民中一些不容易进入工业领域的人口需要我们解决。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。按《宪法》的精神,国家可以去征购公民的土地,把集体所有变成全民所有,但是为了公益性。如果为了商业性,国家征购,地方政府拍卖挣钱,是不符合《宪法》精神的。当然如果规划发生变化,由此产生土地增值的效应,不能全部给土地所有者,但是不管怎么说,我们要重新回来研究这一套东西。
我觉得最好是把土地收入的差额,尽量转移支付给农民。这样农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,社会也更加公平,有利于社会的发展。如果完全回到和农民谈判买地,从法律上讲,他要举手表决,而农民没有严格的组织性,可能什么都买不下来。所以尽管是为了商业目的,我也能容忍国家征购,但是我反对差价。另外还有一个农村建设问题,即建设乡镇企业和城镇化。这一块涉及到财政问题和政府行为。
第三是社会分配不均。我们应该从一个倾向于资本的政策,变成倾向于劳动者的政策,使得劳动力价值能得到更多回报。另外,要把倾向重化工业的政策,调整为倾向服务业的政策。这样居民的收入分配可能更合理,起码在资本和劳动力上,每单位的劳动成本提高了,就业的绝对人数也增多了,居民收入随之增高。
当然还有一条,大家能不能有资产性收入。我们有庞大的国有资产,有些政府在经营;同时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有巨大的缺口,如医疗、教育、社保,很多基础设施也是欠账的。能不能把资产通过资本市场减持,或者划拨给社保资金,这个是可以讨论的。大家如果有资产性收入,也会改善收入分配的差距。
上述三个问题都是由政策和政府行为为主导产生的结果。我希望这些问题被尖锐的提出来以后,会引起一些政策变化,政府职能也会做一些调整。
《21世纪》:你所谈到经济层面和社会政治层面各三点里面,是否具有关联性?
秦晓:经济层面的三个问题,受到地方政府的驱动,地方政府驱动给中央很大的压力。可建立一条幸福指数或者是民生指数作为考核标准,促使政府做增长模式的调整和转换。但所有政策都改变不了中国的生命周期,人口红利就是储蓄多,只能投资,不能消费。
关键在于,是去投效益好的资产用来养老,还是投效益差的项目变成一个泡沫?投资目标好不好,要由市场决定。市场怎么决定呢?若政府把市场要素价格都理顺了,就会有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,居民知道什么能投,什么不能投;如果要素价格都是扭曲的,他就会盲目地投。
(王玉德、郑清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)